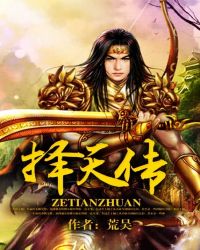苏菲的选择-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许多消费者”?是“一大堆”还是“多如牛毛”?我心烦意乱地在这些枯燥乏味的文字里苦苦挣扎,轻轻念着那些毫无意义的文字,努力控制着自己不去手Yin。不知为什么,这种时候我总会产生手Yin的冲动。最后,我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一边对着那人造纤维板的隔断墙大叫“不!不”,一边扑向打字机,恶作剧般地打出一段另类却不无新颖的文字来:
据统计,在冬季的一个月,如果全北美洲都用“克利尼克斯”手纸擦鼻涕的话,它可以铺满耶鲁体育馆,且厚达一英尺半……
“柯特克斯”卫生纸在美国有惊人的使用量。据计算,如果把四天时间里使用它的荫部连接起来的话,可以从波士顿一直绵延到佛罗蒙特的白水河……
第二天,一向和蔼可亲、宽容温和的范内尔也会对这篇文章惊讶不已。然后,他嘴里叼着耶罗…波利烟斗,脸上堆着善解人意的微笑,对我说:“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想法。”他会让我重写一篇。或许是因为还未在饭碗和爱好之间完全迷失,也可能是因为我身上还残留有一些长老会式的工作伦理道德,那天晚上,我便会倾尽热情和能力提笔重写。但几小时的挥汗如雨后,我仍然只能放弃,重新回到我的《熊瞎子》、《来自地下的记事》或是《比利·巴德笔记》中。要么就什么也不看,只在窗前徘徊,把饥渴的眼光再次投向那座美妙无比的花园:曼哈顿春日黄昏中,温斯顿·汉尼卡特家的一个聚会即将开始(这个漂亮名字是我受洗礼时用过的,现在我用它给这座花园的主人命名)。那是一个我永远无法进入的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这时,金发碧眼的玛维斯·汉尼卡特出现在花园里,身穿宽大的外套和印花紧身便服。她在银白色的月光下站了一会儿,把她那可爱的头发往上梳了一下,然后弯下腰,在花圃上摘下一朵郁金香。她的举手投足优雅至极。她不知道这一切会对一个初级编辑有着怎样的强烈刺激。我的情欲不可思议地剧烈扩张,触手可及。它溜出这破旧的房子,顺着污秽不堪的墙壁滑下,像蛇一样急不可待地窜过篱笆,饿狼似地爬上她那向上翘起的臀部,然后悄无声息地现出我的原形。我带着热切的难以控制的情欲,轻轻地抱住玛维斯,捧住她那丰满、性感、甜蜜的酥胸。“是你吗,温斯顿?”她悄悄地问。“不,是我。”我——她的情人回答说,“让我带你去一个奇妙的地方。”她总是回答说:“噢,亲爱的,是的——等一下。”
在这些疯狂的幻想中,我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和她在阿伯克隆比…菲奇吊床上Zuo爱,但总会有人突然来到花园,打断这一切。比如桑顿·威尔德、康明斯,要不然就是凯瑟林·安·波特,或者是约翰·马奎恩。这时,我从亢奋的情欲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又站到窗前,无比神往地继续幻想下去:在这对活跃的酷爱社交的年轻夫妇家里,有一间与花园平行的起居室(里面,现代丹麦风格的书架上挤满了书,常常惹得我嫉妒地看上几眼),作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们常在此驻足。傍晚,落日的余晖轻柔地洒在花园里,露台上开始出现许多衣着时髦、举止不俗的人。他们谈着某个话题。我甚至能在朦胧暮色中辨识出男女主角们的脸。他们都是我不幸的灵魂陷入文字魔力后,日思夜想、梦牵魂绕的文学英雄。我遇见过的惟一一位作家,就是那位我曾提到过的前共产党交通员,他有一次偶然闯进我在麦克格雷的办公室,满嘴葱味,汗臭扑鼻。因此,在那些春日傍晚,我的想象力在汉尼卡特家频频举行的晚会上肆意放任,那些偶像的面孔疯狂地充斥着我的大脑——瓦特·史蒂文!罗伯特·洛艾尔!一个小胡子偷偷摸摸从门那儿过来了,是福克纳?近期谣传说他在纽约;那个体态丰满,头发挽成小髻,一直咧嘴笑着的女人,准是玛丽·麦卡锡;那个矮个儿、脸庞红润的男子,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只能是约翰·基弗;昏暗的灯光下,一个女人用颤音高喊:“欧文。”这个名字传到我偷窥的地方时,我的心突地一震,这真是那个写《着夏装的姑娘》的人吗?他那如同摔跤运动员般的强壮身体旁有两个女孩子,两张鲜花般的脸庞带着崇拜的神情仰视着他……
我现在意识到,我脑子里浮现的这些人物,都是当时常常在广告或新闻节目中出现,或来自华尔街和其他令人羡慕的行业的名人。但当时的我固执地停留在幻想中。不过,就在我从麦克格雷帝国逃跑之前的一天晚上,我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情感挫折,我的“花园情结”嘎然而止。那天,我又习惯性地站在窗前,把眼光投向玛维斯那熟悉的后部。对我来说,她的每一个细小动作都是那么熟悉、亲切。她穿着那种宽松外套,用手把金发往后撩撩,站在那儿与卡森·麦卡勒斯,还有一个脸色苍白、长着傲慢的英国脸庞的人闲谈着。那人眼睛近视,无疑是奥尔斯德·赫胥黎。他们到底在谈什么呢?萨特?乔伊斯?温特各酒?西班牙南部的避暑胜地?不,他们看来是在谈身边的事,也就是周围的环境,因为玛维斯边说边比划,用手指着那爬满常青藤的花园墙壁、喷水池,以及开满鲜花的郁金香花圃,那美丽的花圃在都市灰暗阴沉的垃圾堆中艳丽夺目。她的脸看上去是那么愉快和兴奋。“只要……”她似乎在说,那张美丽的脸因为不快而越绷越紧。“只要……”她猛地转过身来,朝着大学生俱乐部的方向伸出她那愤怒的小拳头,那苍白颤抖的拳头好像就在我眼前不到一英寸的地方挥舞着。我敢肯定,我能从她的唇形上看出她所说的话:“只要那该死的丑恶的东西不再在那儿死盯着我们!”我懊恼极了。
但我在西十一大街的痛苦命中注定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想到这些,因《孔提基》一事被解职还真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我在麦克格雷走下坡路开始于一个叫威塞尔的新编辑室主任的上任。我背地里叫他“黄鼠狼”,只须把他名字的字母颠倒一下就成了这种动物。威塞尔来这儿是为了给麦克格雷提高一些必要的档次,他那时因与托马斯·沃尔夫相识而在出版界小有名气。在离开斯克利勃和马克斯威尔·帕金斯出版公司后,他开始编沃尔夫的作品专辑,并且在作家死后,帮助整理了尚未出版的大量文稿。尽管我和威塞尔都来自南方,很容易在纽约的排外环境里产生同乡亲情,但我们一见面就相互不喜欢。他是一个秃顶、不太招人喜欢的小个子男人,四十八九岁。我不知道他怎样看我,但毫无疑问,他对我那傲慢的、自由散漫的文风十分冷淡。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呆板冷漠、毫无幽默感的人,脸上总带着愚蠢、自以为是、不可亲近的自负的神气。在办公会上,他最喜欢说“沃尔夫过去常对我说……”,或“托马斯临死前,在写给我的信中意味深长地说……”
他竭力把自己与沃尔夫联系在一起,俨然把自己当作这位作者的翻版。这让我痛苦不已。因为我们那一代有无数年轻的沃尔夫崇拜者,我也狂热到了几乎痛苦的地步。我愿意献出一切,换取与威塞尔共度的一个亲密、轻松的夜晚,以聆听大师的轶闻趣事,尤其是他的那些怪癖行为和惊人之举,以及那重达三吨的手稿。我会不停地惊叹道:“上帝啊,这简直太有趣啦!”但威塞尔简直不可接近。他苛刻、机械,这一点使他与麦克格雷严谨、呆板、极端保守的风气很快融为一体。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仍在那儿自命不凡,玩笑般地对待我的编辑工作。我疲惫的双眼早已变得呆滞,但丝毫不影响我对流行文风、出版业的时尚以及其他一些东西抱相同的态度。因为麦克格雷虽然身披文学外衣,但毕竟是美国式的商业范例,所以,只要像威塞尔一样冷酷的人在这儿掌权,我就知道我的麻烦快来了,我在这儿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
他上任不久的一天,叫我去他的办公室。那张油光可鉴下大上小的枣形脸、纹丝不乱的胡须头发以及充满敌意的黄鼠狼般的眼睛让我产生一个念头,注重仪表乃至到了敏感程度的托马斯·沃尔夫不可能对他有任何信任感。他示意我坐下,稍作寒暄便直奔主题,说我在“相貌”方面不符合麦克格雷公司应该遵守的标准。这是我第一次听人把“相貌”这个词用在形容一个人面容以外的地方。威塞尔又谈到一些细节,令我更加迷惑。因为老好人范内尔从未对我或我的工作说过半句坏话,但现在看来,我的错误还不仅仅在服装上,甚至政治倾向上也有问题。
“我注意到你没戴帽子。”威塞尔说。
“帽子?”我回答说,“是的,没有。”我向来认为帽子是用来御寒的,所以我只在冬季能想起它。两年前离开海军陆战队后,我还从未把帽子与工作联系在一起。戴不戴帽子是我个人的权利。所以,迄今为止,我还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麦克格雷公司的人都戴帽子。”威塞尔说。
“每个人?”我问。
“是的,每个人。”他的回答很干脆。
其实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已经想起来了,麦克格雷公司的确人人都戴帽子。无论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电梯里、走廊上到处都是草编的和软毛毡的帽子。所有人的头发都剪成一样的发式,当然这是对男士而言,女士们(主要是秘书们)就另当别论了。看来,威塞尔的话太对了。我从没发现这一点,但此时我意识到,戴帽子不仅仅是为了时髦,还是一种责任,是麦克格雷公司的一种习俗,就像这绿色大厦里人人都得穿箭牌衬衣或裁剪得体的威伯…黑尔波侬牌法兰绒衬衣一样,不管你是发行员还是编辑。我居然如此愚笨,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与众不同,但即使我现在意识到这些,涌上心头的却是一种既恼怒又窃喜的感觉。我忍不住马上问威塞尔,而且借用他那种严肃的腔调:“请问,我还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吗?”
“我不能批评你的阅读习惯,也不想这样做。”他说,“但对麦克格雷…希尔公司的雇员来说,看《纽约邮报》是不明智的选择。”他停了一下又说:“这是对你善意的忠告。不用说,你当然可以在你自己的时间和地方读你喜欢的东西!但作为麦克格雷公司的一位编辑,你不应该在办公室读那些激进派的东西。”
“那我该看些什么呢?”我问。我习惯在每天午休时到四十二大街买一张《邮报》和一块三明治,然后回到办公室,消磨掉一个小时。《邮报》是我每天必读的报纸。那时我并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只是一个中立者。我读《邮报》不是因为它刊登自由、激进的言论,也不是为了马克斯·勒内的专栏。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我只是对它那大都市报刊的活泼的新闻文风和有关上层社会的报道着迷,比如关于伦纳德·里昂的报道。我在回答威塞尔的时候,知道自己不会因此放弃这张报纸,但可以找一顶卷边的平顶帽戴上。“我喜欢《邮报》,”我说,开始有些激怒,“那你认为我该读什么?”
“《先驱论坛报》也许比较合适,”他慢吞吞、冷冰冰地说,“要么《新闻》也行。”
“但它们都是早上出版的。”
“那就看看《世界电讯报》或《美国纪实》,耸人听闻总比激进要好一些。”
“但《邮报》并不是激进派报纸。”我差点脱口而出,但马上咽了回去。可怜的威塞尔!尽管他像鱼一样冷冰冰的,我却突然有点为他难过。我意识到,不是他想约束我,而是他不得不如此。(这难道是一个南方人对另一个南方人迟来的一点点歉意吗?)他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对这些愚蠢无聊的约束也没一点兴趣。但在那种年龄那种地位,他是麦克格雷真正的囚徒,不得不同流合污,以换取那些不义之财。而我呢,至少我的未来世界是自由、宽广的。我记得他干巴巴地说“耸人听闻总比激进要好一些”那句话时,我几乎有些狂喜地在心里暗暗说道:“再见,麦克格雷…希尔……”
但我缺乏勇气立即走人,这让我至今还为自己感到悲哀。我开始消极怠工,或者确切地说是罢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每天早上准时上班,下午五点准时离开,桌上的待审文稿越堆越高,当然都没看过。中午,我不再看《邮报》,而是到时代广场旁的一个报摊买份《工人日报》。我读它丝毫没有卖弄之意。我一边看,或者说尽量去看,并像往常一样,一边大嚼犹太泡菜和五香烟熏牛肉做的三明治,在这座绿色的盎格鲁萨克逊要塞里扮演着共产党员和犹太人的双重角色。这让我觉得其乐无穷。我怀疑那时的我真有些疯了,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