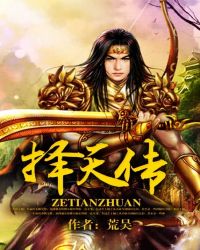苏菲的选择-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金带着一包手稿和两个手提箱来到我的办公室,迈耶小姐说他想见编辑。他有六十岁左右,背有点驼,但很硬朗,中等个儿,因长年呆在户外而变得粗糙的脸上长着浓浓的灰色胡须,嘴唇线条很柔和,有一双我所见过的最忧郁惆怅的眼睛。他头戴一顶黑色皮帽,是帽沿前卷刚好扣住耳朵的那种,竖起的羊毛衣领很厚实可以挡住风寒。他的手非常大,关节又粗又红。他有点流鼻涕,显得十分疲惫。他对我说,他想留下一部手稿。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是北达科那一个叫龟湖的地方,他刚坐了三天四夜的汽车来到纽约。我问他是不是为了送手稿,他说是的。
于是他主动说了起来。他说,麦克格雷是他拜访的第一家出版公司。我问他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他回答说纯属巧合,麦克格雷并不是他想要造访的第一家出版公司。这让我有些吃惊,居然连费金这样孤陋寡闻的作者也没有把它列为首选公司。他告诉我说,长途汽车在明尼阿波利斯停留了几小时,于是他到电话公司去转了转,在那儿了解到曼哈顿的所有电话都刊登在一本黄册中。为了不盲目行事,他用铅笔把纽约所有的出版公司的名称地址都抄了下来。我想,他一定是按字母顺序开始抄的,从阿普尔顿公司一直到齐夫…戴维斯公司。但是,就在到纽约的那天早上,站在波特汽车站惟一的出站口,他抬头一看,祖母绿色的麦克格雷大厦耸立在半空中,上面是巨大的标志,于是他就上来了。
这老家伙看上去已筋疲力尽、昏昏欲睡,还有些惶惑不安。他后来告诉我,他从未到过明尼阿波利斯以东的任何地方,我觉得我最该做的,就是把他带到楼下的咖啡厅。我们在咖啡厅坐下后,他开始讲述他的身世。他说,他的本名应该是“费京”,但后来不知怎么搞的,“G”在发音时被漏掉了。他是挪威移民的后裔,一直在龟湖边的农场里种麦子。二十多年前——他大约四十岁的时候,一家采矿公司在他的农场下面发现了巨大的煤矿矿藏。虽然他们并未马上开采,但与他签订了一个长期租约,足够他后半生享用了。他一直独身,生活一成不变,从未想过要关闭农场。而现在,他有了许多闲暇来开始那酝酿已久的“写作工程”,那便是以他的挪威祖先为主角的长篇史诗:哈洛德·哈法戈——一位生活在十三世纪的伯爵或王子什么的……听到这里,我的心都凉了,但仍一脸严肃地坐在那儿。他拍拍那个手稿包,说:“是的,先生,二十年的心血都在这儿了,都在这儿了!”
()免费TXT小说下载
但紧接着,我对他的看法开始改变。别看他一副乡巴佬的样子,但知识渊博,思路十分清晰,好像还读了不少书,大部分是北欧的神话故事。虽然他最喜欢的作家是不太著名的西格丽特·安德赛特、康特·汉森,以及四平八稳的中西部地区的作家如哈姆林·加兰和威拉·卡瑟等等,但不管怎样,万一我发现了一位天才呢?毕竟,就连惠特曼这样的大诗人,当初不也是像小贩一样到处叫卖他的手稿吗?长谈之后(我已经开始叫他冈德),我告诉他我很高兴拜读他的大作,但我必须提醒他,麦克格雷在诗歌方面并不很在行,然后我们乘电梯回到楼上。当他道别时,我安慰他说,我理解他为这二十年的心血所承受的一切,我将认真阅读这部手稿,争取几天之内给他一个答复。这时,我发现他只打算带走一个箱子。看到我疑惑的目光,他笑了笑,把那深邃、忧郁和困惑的目光投向我,说:“噢,我想你能理解,留下的那只箱子里装着那部长诗的另一半。”
我敢发誓说,这部手稿几乎是人类用手写下的最长的文学作品。我把它拿到邮寄室,让那个男孩秤了秤,一共三十五磅,用了七打哈默·邦德稿纸,共三千八百五十页打得密密麻麻的手稿。长诗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英语,如果你不了解内情,可能会认为这不过是屈莱顿模仿斯宾塞的作品。可那确确实实是在寒冷的北达科那大平原的一间农舍里,用二十年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写下来的。屋外,从萨斯卡切湾吹来的狂风肆虐着田里的麦苗。他一边梦想着他的古老的故国挪威,一边挥笔疾书。
啊,伟大的酋长哈洛德,你为何如此悲伤!
她在为你悲伤,而你又身在何方?
我仿佛看见这位年事渐高的单身汉正在酷热难当的大草原,一边吹着电风扇,一边挥毫写完第四千节。
唱吧,你们这些巨人,还有尼伯龙根但不要再唱哈罗德赞美她的曲调。
请将你们的歌喉充满悲伤绝望:
唱出最恶毒的诅咒!
今天,死亡时刻已到!
——不,它早该来了!
啊,多么悲伤的诗句!
我嘴唇颤抖,视线模糊。我再也读不下去了。冈德·费金还在旅馆等我的回音(我让他住下来等我的决定,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建议),而我却没有勇气拿起电话。终于,带着遗憾的甚至有些伤感的心情,我决定退稿。
也许是我要求太高,也许是这些手稿的质量的确太糟,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不记得我在麦克格雷的五个月里推荐过哪怕一篇作品,结果发生了一件颇有讽刺意味的事。在离开令人窒息的麦克格雷一年多以后,我退的一本书稿(至少我觉得非常糟糕)以芝加哥一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那几天,我常常想象范内尔或是公司其他上层人物的反应。我想我的退稿报告肯定在某位高级编辑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这位老前辈肯定会去翻那些档案资料。天知道他会带着怎样的烦躁与失落心情,重新翻看我那些自命不凡而又冷酷无情的杰作。
所以,在历经几个月的痛苦之后,这样一本散文风格的手稿让我如沐春风。它不再使我头痛、恶心,值得给予一定的赞赏。乘独木舟漂流一定会吸引一部分读者。但我认为,手稿过于冗长和沉闷,像一次乏味的环太平洋航海旅行。如果对它作大量删节,也许可以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之类的杂志上,或让某个大学出版社买下它,但它决不会是我们所需要的书。
我就是这样处理那本了不起的现代冒险经典作品《孔提基》的。几个月后,看着这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不可思议地数星期排名第一,我开始意识到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我想,如果麦克格雷给我的苦力费超出每小时九十美分的话,我对好书与臭钱之间的关系或许会更敏感一些。
在这段时间,回“家”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我住在西十一大街一个叫大学生俱乐部的大楼里,那间陋室只有八英尺宽、十五英尺长。我一到纽约便被吸引到这儿,不仅是因为它的名字,还因为它一周十美元的低廉房租。当我看到这个名字时,涌上心头的是青年团般的同志之情,还有铺着绿色羊毛毯的客厅长桌,上面摆着《新共和》、《党员评论》之类的杂志。当然,这不过是我的想象。大学生俱乐部只在一座低廉的旅馆里占了一小块,门房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他穿一件女人长袍,无精打采地为客人送信件或买买酒什么的。与鲍韦利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个可以锁上的房门,多少有一点点私人空间。除此之外,它与任何一家低级旅馆并无两样。不过,它的位置很好,几乎可以算是别致。在四楼的背面,从我那间陋室里满是污垢的窗口望出去,西十二大街上一座房子的花园尽收眼底。这是一个令人陶醉、心生梦幻的花园。有时,我似乎看见了花园主人——那便是我,一个身着便装的年轻人,他即将成为纽约或哈伯人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那可爱、迷人、身材匀称、金发碧眼的妻子,常常穿着便装或睡衣在花园里跳来跳去,与一条长相滑稽但精心打扮的阿富汗狗嬉戏,或蜷曲着躺在吊床上。在那里,我与她疯狂Zuo爱……
然而,当这一切连同那座傲慢的小花园像符号一般消失之后,大学生俱乐部的破败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而我更是贫困交加,异常孤独。这里的房客清一色是男人,年纪大多在中年以上,多是些流浪汉和穷愁潦倒的人,贫民窟便是他们的下一个去处。他们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地在狭小拥挤、油漆斑驳的走廊中擦身而过,满身酒气,满脸无奈。经常坐在门厅里的不是那老门房,倒是一群卑躬屈膝的死气沉沉的书记员,一盏小灯在他们头上一闪一闪、忽明忽暗。他们不时乘着那部破旧的电梯,大声咳嗽着慢吞吞地爬上四楼。这个春天的每一个夜晚,我都像隐士一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只能这么做,因为我没钱去消遣,还因为我是个初来乍到的乡巴佬,害羞,还有些矜持,既无机会也无情绪去结识新朋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在经过多年的寄宿生活后,我是那么害怕孤独,像一个重刑犯害怕被突然扔进死寂的大牢。我觉得,我现在是靠慢慢消耗多余的脂肪来维持生命。春光明媚的五月黄昏,我呆在大学生俱乐部的小房间里,看着一只硕大的蟑螂从《约翰·多恩散文诗歌集》上爬过,我突然体会到什么孤独,它是那么冷酷、丑恶。
因此,几个月来,我每晚的时间安排一成不变。五点钟离开麦克格雷大厦,在第八大街搭乘地铁来到乡村广场,在拐角处的一个熟食店买点东西。如果钱还够的话,就再买三罐莱因戈德啤酒,然后从那儿直接回到那间斗室,在凹凸不平的床垫上舒舒服服地躺下来。床单已经洗得发白,散发出一股肥皂味。我一边看书一边喝啤酒,直到喝完最后一罐,大约要花一个半小时或更久一些。在我那种年纪,如饥似渴的阅读一如幸福的婚姻成为排谴孤独的最佳方式。在那些夜晚,我只能靠这个打发时光。不过,我又是一个堕落的读者,对几乎所有刺激人的乃至能激发性欲的文字,都有一种饥不择食的喜好。我一点也没夸张。如果与那些承认他们年轻时有此同感的人交流,我想我不会因为这些想法而被别人瞧不起或不信任。我至今仍然记得,那时翻翻电话薄就能让我混上半个小时,我那玩意儿就这样看着那些名字产生轻微而明显的肿胀。
不管怎样,我还是渴望阅读。《在火山下》,记得这是当时最吸引我的书。一直读到八九点钟时,我便出去吃饭。那叫什么饭呀!比克伏特餐厅的索尔兹伯里牛排,吃完后总要留下一滩牛油;有时是耐克煎蛋。有天晚上,我在煎蛋里发现了一根雏鸡的绒毛和还未孵化完整的鸡嘴,差点没把我恶心死。要不就到雅典饭店吃小羊肉。那小羊肉吃起来和老绵羊肉差不了多少,再加上一些有异味的土豆,肯定是从某个仓库偷来的滞销货。但我对纽约的餐厅一无所知,就像我对它的其他很多事情一样。很长时间以后,我才知道这城里“最好”的晚餐,就是白塔饭店的一块汉堡包和一块陷饼,那花不了一美元。
回到斗室,我又抓起一本书一头扎进去,直到清晨来临。不过,我有几次不得不做一些乏味的“家庭作业”,给麦克格雷即将出版的书写些短评。事实上,我被雇用的主要原因,是给出版社一部已出版的大部头作品《克莱斯勒大厦的故事》写了一篇简介。那篇抒情而刚劲有力的文章给范内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显然认为,我必定还能为其他即将出版的书写出同样精彩的短评来。我想,他对我最大的失望,就是我再也没能写出哪怕一篇这样的文章。我一点不了解范内尔,只是从表面上看,麦克格雷那种绝望与消耗融在一起的综合症早已融入他的身心。
我不得不承认,我开始憎恨这种排字游戏一样的工作。我不是编辑,而是一个作家,一个像梅尔维尔、福楼拜、托尔斯泰还有菲茨杰拉德那样充满热情与渴望的作家。有多少个夜晚,他们单独或集体前来与我神会,呼唤我蕴藏于内心深处的作家职责。在扉页上写简介或短评,尤其是为那些带有铜臭味的商业书籍写赞美之辞,让我产生一种沉重的堕落感。下面是一篇我未能完成的短评:
说到传奇的美国梦想,不能不说到金伯利…克拉克纸业大王。在威斯康星一个宁静的湖畔小镇尼纳,他单枪匹马地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金伯利公司如今已是世界纸业几大巨擎之一,在十三个州和八个国家设有工厂,拥有众多的消费者。它的一大堆品牌——当然最著名的是“克利尼克斯”,早已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像这样一段文字要耗掉我几个小时。是用“理所当然的克利尼克斯”还是用“不容置疑的克利尼克斯”?是“众多消费者”还是“许多消费者”?是“一大堆”还是“多如牛毛”?我心烦意乱地在这些枯燥乏味的文字里苦苦挣扎,轻轻念着